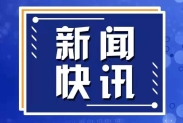“頂流”花花和萌蘭如何“找對象”?科學家有說法了
| 2024-09-01 來源:中國科學報 | 分享: |
熊貓圈粉絲的“心上熊”大明星花花和萌蘭都是高顏值熊。然而,大熊貓繁殖后代一直是一件復雜而頗具風險的事。作為同父異母的兄妹,萌蘭和花花將來能不能找到門當戶對的另一半,將顏值和可愛遺傳給下一代,是粉絲們關心的問題。
8月26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了一篇中國科學家的論文,并入選亮點文章。浙江大學、東北林業大學、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和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團隊,首次系統、深入地對大熊貓進行了保護基因組學研究,為主管部門制定野生大熊貓的保護策略與計劃,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物種保護新策略,同時也給大熊貓“找對象”提供了科學依據。
原來,不同山系的大熊貓通婚需要諸多遺傳因素的評估,秦嶺山系與其他山系的大熊貓通婚更需謹慎;圈養大熊貓后代如果要野化放歸,涉及到跨“山頭”的,更需要基于遺傳基因的評估;盡管熊貓群體數量上升,但秦嶺大熊貓和涼山大熊貓依然是“瀕危”群體……

在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大熊貓在悠閑地吃竹子。
秦嶺大熊貓和四川大熊貓是叔侄不是兄弟
很少有人知道,生活在陜西秦嶺的秦嶺大熊貓和四川大熊貓家族并非兄弟關系,而是叔侄關系。
早在2005年,論文通訊作者、浙江大學教授方盛國對大熊貓進行了分類研究,將中國大熊貓分為四川指名亞種和秦嶺亞種。2021年,方盛國與深圳華大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歡團隊發現,兩個熊貓亞種開始分化的時間是距今1.2萬年到1萬前。
“也就是說大熊貓的兩個亞種家族,已有1萬余年未曾謀面。”方盛國說,秦嶺大熊貓更為古老,但家族成員群體較小,而四川大熊貓家族成員群體更大,遺傳多樣性更為豐富。
大熊貓生活在6大山系——秦嶺、岷山、邛崍、大相嶺、小相嶺、涼山。但是,六大山系的大熊貓并沒有隨著山系被分割成六個種群。他們發現,四川大熊貓不同群體生活在不同山系的高山峽谷,千年來沒有通婚,形成了不同的遺傳支系,分別為岷山種群、涼山種群、邛崍—大相嶺—小相嶺種群。
這一次,聯合團隊對大熊貓進行了大規模高質量的全基因組重測序和群體基因組學研究,構建了迄今為止最精細的大熊貓遺傳變異圖譜,揭示了大熊貓六大山系野生種群的遺傳結構,發現了顯著遺傳分化的新亞群結構,模擬了人工圈養繁育子代放歸野外的遺傳風險。
論文第一作者、東北林業大學教授蘭天明告訴《中國科學報》,在四川亞種內部,涼山與其他種群之間的隔離分化時間最早,發生在距今1.10~0.62萬年前;岷山與邛崍—大相嶺—小相嶺種群之間的隔離分化時間發生在距今0.60~0.35萬年前。
在整個隔離分化過程中,還發生過多次基因交流(指交配并產生后代)事件,特別是秦嶺個體遷入岷山種群,涼山個體遷入邛崍—大相嶺—小相嶺種群。這些分支種群之間的基因交流沒有完全中斷,同時又能在獨立的地理單元進行獨自的隔離進化,豐富了物種的基因多樣性。
秦嶺大熊貓和涼山大熊貓依舊“瀕危”
而物種的基因多樣性對物種的存活至關重要,簡單來說,就是多樣性越豐富,物種越不容易瀕臨滅絕。
他們發現,大熊貓整體的近親交配(以下簡稱近交)和遺傳多樣性喪失問題并不嚴重,在野生動物領域處于中等水平,遠遠低于東北虎、華南虎等物種。
“但不同種群的近交程度卻存在差異,其中秦嶺種群的近交和有害遺傳突變的積累最為嚴重,涼山種群次之。”論文通訊作者劉歡說。
方盛國強調,大熊貓秦嶺種群和涼山種群亟須重點關注。秦嶺大熊貓經歷了持續性的種群衰退歷史,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秦嶺地區不僅是華夏文化的發祥地,而且近千年來人口密集、戰爭頻繁,嚴重影響了大熊貓的棲息繁衍。
另一方面,大熊貓主食竹子北界南移,加之持續近交,導致基因組不斷純合化,種群遺傳多樣性日漸降低,強有害突變造成幼崽早期夭折,弱有害突變純合化積累,導致種群環境適合度下降,從而導致持續性的種群衰退。
“第四次全國大熊貓野外種群普查發現,秦嶺山系適宜大熊貓生存的棲息地顯著低于其他山系,亟須關注秦嶺大熊貓的保護工程。”方盛國說。
涼山大熊貓也是一個相對孤立的古老種群,有效種群數量較小,遺傳多樣性喪失、近交和有害突變的積累僅次于秦嶺種群。在上世紀50~90年代,涼山種群還經歷了一個快速減小的特殊時期。
盡管近20年來,我國對涼山種群實施了有效的保護措施,但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國大熊貓普查結果顯示,涼山種群的數量增長程度和棲息地人為干擾的減少程度都是最低的。
蘭天明告訴《中國科學報》,目前,涼山種群在地理上被隔離成了5個不相連的小種群,且2個最大的隔離種群離開發用地較近,另外2個小的隔離種群處于孤立狀態,很難與鄰近的大種群連通產生足夠的基因交流。而且,目前涼山大熊貓棲息地尚未規劃到大熊貓國家公園建設中去,涼山大熊貓的保護工程也面臨諸多困境,未來種群的近交風險和滅絕的可能性亟須受到特別關注。
方盛國強調:“應充分認識到秦嶺大熊貓種群和涼山大熊貓種群受到生存威脅的程度,仍然是‘瀕危級’,亟須學者、管理者、政府和國際組織的特別關注,萬萬不可將所有的大熊貓野生種群視為一個整體進行降級對待。”
不同山系的大熊貓通婚需謹慎
他們對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和秦嶺大熊貓研究中心的7個主要繁育譜系的圈養大熊貓樣本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圈養大熊貓后代出現有害突變的風險比野生大熊貓更低。
“這表明科學的圈養譜系管理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近交,保護圈養個體良好的遺傳進化潛力。”論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李仁貴說,圈養大熊貓婚配的時候,也應當考慮其祖先屬于哪個山系,不同山系的大熊貓之間通婚要做大量婚前遺傳檢測,不宜隨意婚配。
此外,圈養大熊貓繁育后代的野化放歸,是大熊貓保護工程的遺傳拯救策略之一。論文共同第一作者、浙江大學博士楊尚辰指出,遺傳拯救工程中有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放歸個體可能攜帶了受體種群沒有的有害突變,這種新引進的有害突變有可能在受體種群中擴散,導致受體種群的有害突變進一步增加。尤其是長期分化的種群之間再次恢復基因流,很可能會因為引入不能適應當下環境的基因,加速小種群的滅絕。

中國第一只成功野化放歸的大熊貓淘淘和它的媽媽草草。李仁貴供圖
劉歡強調,經過模擬評估,他們認為,放歸本山系圈養繁育的后代個體,是小種群遺傳拯救的最優先策略,因為它可以避免不同山系種群環境適應性帶來的風險,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后代個體的有害突變。
因此,對于秦嶺、涼山和岷山山系北部的小種群,野化放歸的個體應該盡可能選擇有各自山系背景的圈養繁育后代,或野外救助的大熊貓;對于大相嶺和小相嶺這2個山系,由于其與邛崍山系同為一個遺傳大分支,所以可以從邛崍山系圈養大熊貓的繁育個體中,挑選遺傳背景相似的個體進行放歸。
蘭天明強調,在野化培訓之前,應對放歸個體未來繁育后代進行遺傳模擬預測;放歸后對后代進行基因組和表型各項指標的監測。這樣可為野化放歸提供最具價值的科學數據,并通過不斷修正并完善放歸計劃,構建大熊貓野化放歸的完整體系。